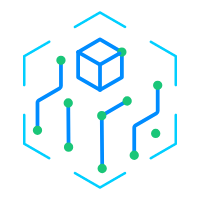冯川强宗大族与弱宗小族宗族性社会的内在差异与本质
冯川强宗大族与弱宗小族宗族性社会的内在差异与本质
提到宗族性村庄,往往首先想到的都是位于广西、江西或者福建的强宗大族,因为那里的宗族符号性特别明显,符合我们对于宗族性社会的想象。这里以赣南L村为例:
1、单姓主导,房头发达。典型的宗族性村庄,村内血缘与地缘相互重叠。这样的单姓村内甚至可以聚居几千上万人,他们分成好几个房卡(徽誉搬家)。比如L村人口规模达00多人,下辖22个村民小组。“宋”姓是村庄主导姓氏,已发展0多年,分为仁(成都异地搬家)、义(宣化搬家公司电话)、礼(衡水搬家公司电话)、智(顺利搬家电话)、信(庇护所搬家)共5个房卡。其中二房和小房人数多,是典型的“大卡”。
2、祠堂系统复杂。在典型的宗族型村庄,“祠”与“堂”有着严格的区分,并且“祠”不但因辈分而具有“大祠”和“小祠”、“总祠”和“分祠”的层级性,而且可以继续不断被再生出来。所谓“祠”是设立神龛供奉特定祖先牌位的地方。比如在L村,整个宋姓有一个总祠,人数较多的二房和小房也有自己的分祠,二房下面又有分祠。村民春节拜年,一上午就要跑4、5个祠。“堂”则是没有设标识特定祖先的牌位、只设了上书“历代高曾祖考妣”这种泛指一个群体概念的牌位的地方。在当地每家每户的厅堂内,都设有这样的牌位,村民称其为“家神牌位”。因此可以认为,每家每户的家中祖厅都是一个“堂”。
村民认为,“家神牌位”是不用另外去拜的,“家神只管我和我的子孙”。他们每天吃的k22碗饭(搬家吉日一),都会用来供奉家神。他们还会在农历每月初一、十五,在家神牌位旁点香。从祭拜关系上看,如果说“祠”是活着的多家人在非日常的特定时间祭拜一个去世的人,那么“堂”就是活着的一家人日常性地祭拜去世的多家人。每一个男性村民都有“开枝散叶”也就是“开卡”的可能性,因此都有可能成为子子孙孙所供奉的人。因此,每一个“堂”都有可能在若干代之后自然演化为“祠”,每一个活着的男性村民都有可能成为“祠”的主人。
3、重视修谱,看重“上家谱”。在修谱方面,宋氏第3次修谱还是在解放前,19年第4次修谱。当时是宋氏家族中辈分高、年龄长的家族成员提出,要组织-年龄段的几个他们认为有能力和威望的人修谱,因为“别的姓氏都修谱了”。这些人就组成了最初的理事会,有修谱经验的长辈会对修谱提出意见。
在上家谱方面,招赘结婚以前需要写《搬家怎么接火》,规定“以后若生了儿子,生了一个就是每人一半,在夫妻两边各上家谱”。L村有一例招赘婚,生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女儿都随父亲姓,也上了父亲那边的家谱;儿子随母亲姓,但在两边都上了家谱。而在过继的事例中,小爷爷过继爷爷的孙子做长孙,过继者需要负责小爷爷的生养死葬,但一直不和小爷爷一同生活。在族谱上,爷爷的儿子名字同时会写在爷爷和小爷爷两边的名下,而过继者作为小爷爷的长孙,名字只写在小爷爷下面,过继者的后代也都写在小爷爷这边。
出生。生了小孩的家里要准备一坛酒,杀一只鸡,到祠堂“报新丁”,在祠堂祭拜。
结婚。起码每桌要有20斤猪肉,7个“水菜”猪脚,瘦肉,猪杂,竹笋,烧鱼,焖鱼,鸭。没有青菜,还有3盘可以带走的“荒菜”。
乔迁,有进火仪式。祖宗从过火以后,到新的地方延续香火,也有基业扩展的意味。送火仪式,是在老房里面进行,老房的邻居、兄弟跟在老房主人后面放鞭炮,男主人挑箩筐在最前面,箩筐一边装厨房里的锅、煮一口饭,一边装放谷子的金器银器,点上香炉放在箩筐里;妻子拿着锅铲、火铲;儿子、孙子,背上书包、背上木梯,意味着步步高升;儿媳代表性地拿剩下的。接火仪式在新房厅堂举行,老房邻居也参与。
男主人挑灶具到门口时,其他人在新房把香烛点起来:1对香烛、5支香,插在家神位香炉,鞭炮一直打进来。所有的送火女性,用火把点捆好的柴火放到灶里。用红纸,包一点老房子的香炉灰,带到新房子的香炉里,老香炉要留在老房里不能搬。接火仪式进行前,老房子也要点香烛和线香。男主人会跪在老房,对祖先讲“上代的列祖列宗,你的子孙XX建了新房,你也可以到那里享受享受”,然后装线香。如果老房没人住,香炉要一直留在老房,不过不一定会点,除了过年、中秋、元宵的时候杀鸡去,点一下香火,其他时候不去。
白事,会请一个风水先生,按照死者年龄取一个日子,安排入棺、出葬的具体时辰;请八仙负责抬棺;由本家族长辈担任礼生,负责引导祭奠仪式的流程。盖棺以前,不能放在厅堂里。岁以下去世的(北京工厂搬家),盖棺前要放在前厅有“三进”的:前厅、中厅、上厅。
墓碑碑文规定,岁以下去世的:男人只能写“宋XX老先生”;女性写“老秋香”。岁以上去世的:男人写“宋XX老大人”,女性写“老孺人”。对自杀者,没有规定。在自己家的房子外死的(兖州搬家公司价格表),灵位可以进祠堂、包括自家整个房子,尸体不能进祠堂、自家整个房子。因为死人只能搬出去,不能搬回来。死人咽气前,所有子孙要围在周围看他咽气,叫“送终”。时间来不及,突然去世,就在其他房间,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要死。有时间的,一般都要在厅堂里咽气,快要死的时候把他自己连睡的床搬到厅堂里去。厅堂是去世的归宿点,其他房间是没有死的人才居住。有的在厅堂要几天才去世,有的又活过来了。
祭祖。在解放前,清明祭祖要做20天,因为每个房、每个卡都要祭拜。到了现在,清明时一个村民也需要去好几个祠堂祭拜。
5、村际群体性冲突发生风险高。在解放前,宋姓主导的L村与黄姓主导的W村,经常因风水冲突和地界纠纷而发生大规模械斗。近年来,新农村建设规划不讲方位,又激起两姓之间的群体性冲突,在风水地界上“谁也不能断定谁有没有道理,你讲有妨碍我说没妨碍”。此外,2012年由于黄氏家族建门楼,宋氏家族认为黄氏的门楼侵占了宋氏土地,宋氏祠堂理事会组织族人准备去与黄氏族人打架,最后镇长和派出所所长出面调解,使黄氏门楼向后退让了几十米,虽然仍在宋氏所声称的地盘。村民说,如果不是出面,在以前一定会打起来。
然而,宗族性社会中并不全是强宗大族,甚至于绝大多数都不是理想中的强宗大族。宗族性社会的版图内部也并非是铁板一块,其社会样态其实也是充满差异的。如果我们对宗族性社会的刻板印象全都建立在我们对于强宗大族的认知和想象之上,那么调查弱宗小族的宗族性社会将会打破我们对于宗族性社会的刻板印象,以证伪的方式丰富我们对于宗族性社会的认知。这里以地处潮汕地区的粤东Z村为例:
1、宗族性村庄的秩序并不一定由单一姓氏绝对主导和整合。在我们的刻板印象中,宗族性村庄社会内部理应是被“宗族”这个单一姓氏集团高度整合的庞大的“团结型社会”。然而Z村不但规模小,全村人口总共也只有9人,分为上下2片,也就是2个村民小组;而且上下两片还各有一个主导姓氏:上片(武汉居民搬家)的主导姓氏是刘姓,300多人,小姓包括彭姓几十人、陈姓几人;下片(香坊搬家公司)全部姓吴,有0多人。
村庄内部不存在k22的主导姓氏,不论是村委会干部的构成,还是村民代表的构成,都显现出两大主导姓氏平分秋色的平衡关系,甚至连村聘干部的来源也要考虑对两大姓氏集团的平衡问题。至少从外在表现上看,村级治理需要面对的不是由单一主导姓氏结构性地生产出来的“团结型社会”,村庄社会的初始状态相反更偏向于一种“分裂型社会”,有待于村级治理者的后期整合。
在多姓切割之外,“通婚圈”的扩展也冲击和再造着父系宗族在村庄内的整合秩序。通婚,即是形成以“姻亲关系”以及附着其上的亲戚往来。在以遵循纵向结合原理的父系血缘关系为明线的搬家策划络之下,其实还潜藏着由遵循横向结合原理的姻亲关系编织而成的暗线。这条暗线一方面在事实上扩展了父系血缘关系主导的搬家怎么接火络,但在另一方面,姻亲关系实际上也弱化了房头,使宗族关系更为复杂。
Z村村民在谈论社会关系时,常提到“亲戚朋友”。比如,作为小姓的陈姓在办理白事时,会“找亲戚朋友”,“亲戚送一些钱,主家人没钱也能把仪式办下去”;上片和下片各自在拜完老爷或妈祖之后,“亲戚朋友会聚一下”;上下片之间,会因亲戚关系而相互走动;红事办酒,都是请自己的房头和亲戚。而在结构性强、建构性弱的典型宗族地区,除了仪式性人情之外,村民的日常生活中是很少提到“亲戚朋友”的。
② 片内通婚。上片的刘、陈、彭三个姓氏之间相互通婚,形成“都是自己人”的认同感,起到了整合片的作用。
③ 片际通婚。19年代前,上下片之间不能通婚。其后通婚,生产出亲戚关系,最后促成上下片村民间的日常性走动。起到了整合行政村的作用。
因此,Z村形成“血缘关系—姻亲关系—朋友关系”的社会关系圈层。其中,血缘关系只是满足基本需求,是个人生活的后盾,但相对缺少情感性的表达和交流。
而姻亲关系的功能,核心在于打破血缘边界,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进行利益、信息和资源的关系建构,进而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整合社会、整合市场。具体而言:
一是作为社会整合力量,扩展利益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的边界,最终扩展集体行动的群体边界。
二是作为信息交流通道,与新信息相联结,促成本地的农业转型和新技术的传入。比如与邻镇若有亲戚往来,就可以在没有乡镇指导的条件下,靠姻亲关系构建的私人关系学技术。Z村的茶产业最初就是凭借姻亲关系从邻镇传入的。
三是作为资源传送通道,与外部资源相联结。Z村村民之所以能够走出村庄外出务工、在乡镇开手工作坊、在更大的市场范围内当茶叶收购批发商,村际、镇际姻亲关系的建立功不可没。而本地的“凤凰单丛茶”之所以形成为一种更多面向潮汕本土的区域性品牌,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与一般限定在潮汕地区内部的本地属性通婚圈有关。
朋友关系,则是在有急需时寻求帮助的对象,比如借钱的对象,同时也是开展情感交流和情感表达的对象。
总而言之,宗族性村庄的整合力量可能比单一姓氏的绝对主导模式要丰富得多。在血缘关系之外,姻亲关系和朋友关系的存在都能够用以满足个体不同的需求和期待,因此在不同层面参与对宗族性村庄社会的再塑造。由于认同单元过于多元而不集中,削弱了单一血缘系统的整合作用,村民之间更多是处于熟悉而不了解的“半熟人社会”状态。
2、宗族性村庄并不一定有复杂的祠堂系统,甚至一个祠堂不一定只由一个姓氏使用。在Z村,村民中不存在“祠”与“堂”相区分的观念,因为村民家中一般没有家神牌位,因而不存在“堂”,也不存在从“堂”演变为“祠”的再生产机制。调查了解到Z村吴姓有5、6个房头,刘姓有16个房头。又得知,最初Z村上片陈姓和彭姓各有一个祠堂,刘姓有4个祠堂。在“破四旧”运动中,许多祠堂被拆毁。改革开放后,上片三个姓氏就合拜一个祠,即“合祠”。而下片吴姓也只有一个祠堂。
正因为不存在从“堂”演变为“祠”的生成机制,同一个姓氏最多只有二代祖分房头后形成的若干祠堂,比如最初刘姓的4个祠堂。而后代即使再分房头,也就不再生成新的祠堂。甚至一个姓氏就只有纪念初代祖的k22一个祠堂。弱姓、小姓可能没有自己独立的祠堂,“合祠”显示出大姓对小姓的庇护,表明大姓不会对小姓形成排斥和欺压之势力,小姓在大姓主导的宗族性社会里也不会感到压力。
3、宗族性村庄并不一定存在族谱,更没有“上家谱”的概念。在Z村,没有一个姓氏可以拿出自己姓氏的家谱出来。村民说,姓氏集团内部也不存在“族长”或是“长老”,大部分人对自己家族的历史并不了解得十分清楚,只是模糊知道祖上是从福建迁过来的。总体而言,村民对村庄社区的历史记忆并不长,因为历史记忆对于他们的生产生活而言并不重要。
族谱的意义除了保留家族的历史记忆,更在于确认辈分秩序,形成长幼有序的伦理格局。一般而言,宗族社会内部不存在同姓通婚的现象,为的是维系亲属称呼制度的稳定性。如果不这样做,比如出现与自己的姑姑通婚的情况,那么如何称呼他们的孩子就会成为挑战亲属称呼制度的问题,这意味着对既有社会秩序的扰乱。然而,Z村内部存在被村民视为正常现象的同姓通婚。虽然没有族谱,但他们都能确认同姓通婚不会发生在共一个太爷爷的三服亲属范围之内。他们认为超出三服亲属范围之外同姓通婚是不存在问题的。这说明在不存在族谱的Z村,不但村庄历史记忆会随着世代的累进而被不断删除,而且血缘关系也会随着三服亲属范围的不断下移而陌生化。
4、宗族性村庄并不一定会频繁举行公共仪式,仅有的公共仪式也没有繁复而确定的仪式规则。
白事。只办一天,第二天就上山了。不做道场,只请风水先生看朝向。2000年左右开始全部实行火葬。整个过程没有人领头,主家会通知各房头商议分工。
祭祖。春节时,家族成员到祠堂上香祭拜。清明时,三服以内成员自发组织起来一起去坟地。坟地没有墓碑,都是土堆。因为每年清明都会祭扫,村民们不会忘记坟墓的所在地和埋葬者的身份。但在几代人之后,前面世代的坟墓必定被遗忘。
拜老爷。是上片人自发进行的仪式活动,时间一般在元宵节、中秋节。祭拜本身不需要组织,各家各户的全家老少都会带着猪肉、水果和三炷香去祭拜,拜完回家还要放鞭炮。上片的4个老年村民自发组成的“老人组”分别为、、、岁,都是上片的男性村民会组织20多个30-40岁的青年人打锣鼓、抬老爷。上片的其他热心人士f4b胶南搬家f5b,会在拜老爷前后3天请人来唱戏、放电影。下片的村民也可以去看戏、看电影。
拜妈祖。是下片人f4b汉口蚂蚁搬家f5b自发进行的仪式活动。下片没有“老人组”。但吴姓内部也能组织下片的村民开展抬妈祖的仪式活动。
5、宗族性社会的群体性冲突并不一定发生在村与村之间。因为宗族性村庄内部不一定只有一个主导姓氏,在存在多个主导姓氏的情况下,群体性冲突自然更容易在村庄内部出现。在Z村,上片以前叫刘厝,下片叫吴厝。显然上片在地名上省略了陈和彭这两个小姓,也就是说,刘姓作为主导姓氏吸收了另外的小姓。上片村民说,上片三个姓氏之间很久以前就相互通婚,打破了姓氏相互区分的格局,因此“上片内部很和谐,没有姓氏隔阂,都是自己人”。而上下片之间直到19年代还不能通婚,甚至一些老人为了阻止通婚限制的打破还打过架。一些熟悉村庄历史的村干部介绍,“原来上下两片之间是很不和谐的,经常打仗”。
那么,既然弱宗小族的种种表征都不符合我们对于宗族性社会的想象,为什么我们仍然能够将其界定为宗族性社会?这就需要进一步反思:我们所说的“宗族底色”,其本质究竟是什么?
强宗大族所突显出的符号性色彩,使其社会形态更具有表达性。而在弱宗小族的村庄,这样的符号性色彩明显弱化。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宗族性社会内部,差异化的表达方式和表达能力其实是宗族的常态。我们应该透过“不一样”的常态,找到不同宗族性村庄背后的相通之处。
所谓“宗族”其实是一种社会组织形态。而不仅是宗族,任何组织如果能够存续,就一定意味着该组织存在功能性,因为一个不具备任何功能的组织一定会走向消亡。那么,宗族与一般组织的区别在哪里?其实是在与宗族所独具的伦理性,以及伦理性与功能性的关系。宗族组织的功能发挥,是以伦理性为支撑的。宗族性社会的伦理性托举了功能性,如果没有伦理性的底色,宗族性社会的功能性就建构不出来。而伦理性的核心,是公共性。
公共性是一种价值,它认为存在一种目标可以超越“小我”之私、可以优先于“小我”之私。这种价值可以转化为宗族组织的功能,并通过宗族内部的互助、资源分配和资源争夺等行为和事件展现出来,而互助、分配、争夺便是宗族组织的主要功能。这些价值性行为的躯壳背后,是利益性联结,这与村庄内部的治理资源密度和治理需求紧密相关。而宗族所承载的“血缘”本身就是一种治理资源。一旦村庄面临治理资源不足和治理需要,“血缘”就可以成为被进一步开掘的治理资源,宗族的各种符号性特征也就可以“借尸还魂”。
因此,综合上述逻辑,我们可以认为宗族性社会的核心不是诸如族谱、械斗、仪式之类的符号性表达,而是公共性。粤东Z村本身的村庄利益稀薄,因此宗族性符号的表达性不显现。但是,Z村靠近低端劳动力密集型市场,村民可以频繁返回村庄生活,进而能够保持村庄社会关系的完整,以至于村民对村庄有着基本文化认同,村庄仍能进行在地化的精英再生产,将有公心的人识别出来。
其结果便是,诸如人情、面子、血缘、互惠关系在内的公共规则能够在村庄内部得以维系,有公心而不是有钱成为个人权威性的来源。所谓“公心”,即是一种超越私人性关系的公共性人品,人品是否具有公共性,是当地人判断人品好坏的重要标准-k22人品具有公共性,就是人品好;人品好,自然在村庄里就有面子。当然,如果在有公心的基础上有钱,为了公共利益而多投钱,就会换来更多的尊重。进入老人组的老年人是村庄内生权威的象征,对年轻人能够产生示范作用。以公共性为判断标准,我们可以认为粤东Z村虽然在宗族的符号性表达上存在与赣南L村的诸多不同,但它仍是宗族性村庄中的类型之一。
一是层级性。根据公共性的涵摄范围,以Z村为例 ,层级的公共性是面向整个行政村的公共性,k22层级的公共性是面向整个家庭的公共性。中间层级的公共性,则包括层级稍高的面向整个片或整个自然村的公共性,以及层级稍低的面向整个房头的公共性。层级越低,公共性的维系和再生产越会以一种自发的、日常性的方式进行。层级越高,公共性的维系和再生产的自发性和日常性就会减弱。
比如中间层级的公共性,其维系和再生产需要依靠来自宗族社会的血缘关系以及以此为根基的社会伦理价值的支撑。而到了层级,公共性的维系和再生产就需要一种超越血缘关系的政治认同加以支撑。村干部在将层级的公共性植根于宗族性村庄社会内部方面,以其半行政半自治的身份特征,发挥了关键的作用。然而一旦村干部这种“植根”的作用力度弱化,层级的公共性就很容易悬浮于村庄社会,成为对接国家行政体系的村干部个人的公共性。
明确层级公共性与中间层级及其以下层级公共性的差异,有助于解释一个宗族性社会的常见现象:为什么宗族集体行动往往在修祠堂、拜老爷等方面表现积极,却在修路、修水利等方面表现消极?
这是因为,修祠堂、拜老爷属于建立在血缘认同和以此为根基的社会伦理价值之上的中间层级的公共性,宗族血缘关系的整合力度对个体参与集体协同行为造成一种社会压力。而修路、修水利则属于超越血缘关系整合范围的层级的公共性,动员群众的行政整合力度决定层级公共性在村庄社会中扎根的深浅。
一旦村干部不再动员社会内生力量参与这些公共品供给,层级的公共性就很容易脱离村庄社会本身,变得与群众的日常生活感知和认同结构无关,层级公共性就会变成村民口中的“公家的事情”。在大量村级公共品建设通过自上而下的项目制资源加以达成的当下,村干部在村级公共品供给方面一般不再让村民插手。最后,村级公共品供给脱离了社会内生力量的动员,或者依靠行政体制内部的资源输入;或者依赖市场规则,比如村干部在过节时花钱请勤快的村民打扫村庄卫生;或者依赖村干部的自我消耗,比如平时村干部亲自打扫卫生,在公共品供给资金不足时亲自垫资。
当然,宗族性社会公共性的层级性,与宗族村庄的血缘结构密切相关。非宗族性社会也可能存在公共性的层级,不过在非宗族性社会,由于公共性建构往往缺少以血缘结构为基础的内生建构模式,其所展现的公共性层级更多是一种以地缘聚居形态为基础的行政建构层级-k22村民小组层级的公共性,以及行政村层级的公共性。
比如,成都公共服务资金体现的是以制度输入为手段的公共性国家建构模式,其所建构的是以“村级议事会”为载体的面向整个行政村的公共性,以及以“组级议事会”为载体的面向整个村民小组的公共性。而在盛产脐橙的宜昌,则存在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而建构的公共性。聚居于同一个村民小组的村民基于脐橙种植的共同利益,共同出资修建机耕道,这体现的是一种面向村民小组这一办公室搬家计划社时期生产小队的行政建构层级的公共性。在非宗族性社会中建构公共性的方式,对宗族性社会中如何建构面向行政村且能扎根宗族社会的公共性具有借鉴意义。
二是相对性。宗族性社会的公共性具有相对性,即“公”与“私”在不同的场景下可以发生转换,形成一串前后相续的谱系结构。“公”的主体性越强,就意味着“公”与“私”的相对性越强。在家庭内部,父母相对于子女而言是不容挑战的“公”,子女是“私”;在宗族内部,宗族相对于父母是“公”,父母是“私”;在行政村内部,基层组织相对于宗族是“公”,宗族是“私”;国家相对于基层组织是“公”,基层组织是“私”。居于上位层级的主体相对于居于下位层级的主体而言是“公”,能够自上而下发挥融通、整合的作用;居于下位层级的主体相对于居于上位层级的主体而言是“私”,其核心意志是“分”,的是“公”的主体如何将整合的资源进行合理分配。
三是分别性。虽然在资源的整合与分配上,“公”与“私”能够以公共性的相对性为基础,形成“公”与“私”的连通;但是在被认为属于“私”的具体事务方面,“公”往往不会主动介入进去,体现出“公私有别,内外有分”的特征。近年来,宗族性社会中“私”的主体性也越来越强。“私”的主体性越强,就意味着“公”与“私”的分别性越强。
在调查访谈中,我们发现村民对于别人家的家事不愿意过多谈论,经常以“不知道”“不想说”搪塞过去。村民也不太愿意谈论自己的家事,比如有一个媳妇在谈论了自己的家事后对我们说“千万不要告诉我家老公,他不让我给别人讲自己的家事”。这都说明,村民普遍认为家庭内部关系的性质是“私”,一般是不能进行公共讨论的事情。代表“公”的村干部也被认为不能轻易介入村民的家内事务,因为属于“私”家内事务应该由家内成员自行解决。
表现为强情感性的核心家庭作为“私”,其主体性增强的表现是:在承认大家庭的“公”对“私”的融通整合结构的基础上比如儿子认同“父母再不对,也对”这句话,即虽然自己的理性判断父母不对,但仍然服从父母的公共性权威。觉得父母做得不对,儿子也不会批评,除非父母自我反思、自我批评,年轻夫妇运用分别唱红脸、黑脸等配合策略,从“公”的掌控中逐渐分离出不受“公”的过多介入的小家庭主体空间。